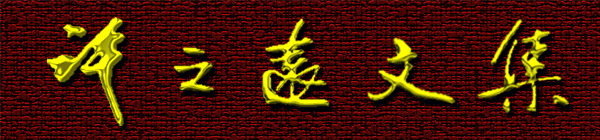
|
|
|
|
《二十九》告別臺灣
也算禍棗災梨 學生時代的日子過得真快了;一幌間,四年很快就過去了。世間最貴重的寶物,更多的金錢,都無法把時間挽留得住。 四年來學到甚麼?想來有點徨恐,學問是談不上的。最多只能說找到做學問的門徑,和懂得理性的思考。經濟系有關的必修科想來不少,除了和其他院系共同必修科外。本系生主修的有經濟原理,經濟政策,會計學,統計學,貨幣銀行學,微積分,政治學,法學緒論,中國經濟史和西洋經濟史等。選修科的學分,是用來補充學位所必須的修滿便畢業,是有選擇性的。由於分數至上的風氣,大家選分數易得的科目,其他因素都變成次要的考慮,這無疑是大學教育的一個缺失。四年來在學生刊物發表過的文字,搜集起來也不少。經過整理和刪訂以後,向救國團文教組請求出版單行本。很快便批準,和僑委會共同補助,這是我第一本著作──「火花」;終於出版了。這本學生時代的作品,肯定是不成熟的,但它終究是人生的一個歷程。我急不及待連學士照一同寄回香港給父親,他高興得寫了一首長詩來勗勉。我來加後仍保留下來,可惜近年幾經搬遷,竟亦失去了。 我們這一系應屆有一百六十多位同學,除了我以外,尚有兩位在學的時候出過單行本了:一位是劉本傑,另一位是潘紹周。劉本傑兄畢業後到美國留學,得了經濟學博士,現在任教美國。近年不時還讀到他在國內發表的經濟論著,也參加過國建會,看來他還充滿朝氣和活力,並且學以致用。比起我這個也學「橫眉冷掃千夫指」的人高明許多了。 潘給周兄畢業後到加拿大留學,由於要服兵役的緣故,比我遲了些日子。他是江蘇人,有江南人物的靈秀,聰明得很,過目不忘。但少了一份剛毅,也許是聰明人普遍一種毛病。得了學位後便在當時中華民國大使館任職,因此住在渥太華,不久到多倫多來,可惜英年早逝,才人如此,悲夫。 日常慣見亦美人 由於「火花」的出版和應屆畢業,幾位熱心的同學為我籌辦一個舞會來慶祝的,連舞伴也措著代籌。 開舞會在學生時代是最簡單不過。找一個適當的課室或活動中心,一部唱機和幾個唱碟就行了。佈置和茶點是豐儉隨意的。我個參加過一些「克難舞會」,一杯清茶,幾粒花生米,就可以跳一個晚上,沒有人說一句芥蒂話了。同學間那份清純的情誼,入了社會以後再回頭想想,就更感到珍貴。 舞會的佈置和招待,全由海風社的學弟們為我打點妥當。請的都是有交誼的同學,羅有六、七十人,其中有小部分來自師大。 即使在二十多年前,臺灣還在克難時期,但參加舞會的女生已打扮得不錯,畢業班的女生就更注意。同班的幾位女同學,以李湘捷最惹人注意,她美好的身段和刻意的打扮,使我們男生的眼睛發亮。 怎也想不到平日荊釵裙布的她,竟會這樣漂亮。她出生的那一年,正是抗戰時的長沙大捷,所以叫做湘捷。也因此,她常常說:我的年齡最老實,你們一聽我的名,查查年份就知道了。成嘉玲是我國著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,她在班上不但成績好,還唱青衣,在學校平劇社演過「坐宮」的公主。畢業後到夏威夷大學研究,得到博士學位。現在回臺,主理她的父親所創辦的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」。此外,同班的譚靜如、趙淑燕、劉筱潼等,畢業後都到美國留學去了,統統失去聯絡。不同系的也不少,法律系的劉雲,後來到美國唸會計,現居三藩市,還是那樣瀟灑奇磊。師大的施小曼,早幾年還在多倫多,到雲高華真光中學聘她到那裡執教,她就急不及待,全家一起跟著她去了。她對僑教有一份執著和熾熱的心。 一拳打出前途 同班的好友也實在不少,大概與我好結交朋友的性情有關吧。全班最高的董興兄,總有六尺過外,與我十分投契。也真難為他,我們時常一起走路,遇上談話的時候,他只可把脖頸盡量彎下來。他是個漫畫能手,出過一本漫畫集,集中的序還是我寫的。他是我國甲骨文先進專家董作賓先生的兒子;我好幾次到過他的家,畢業的時候,興兄向他的父親,要了一張小條幅的甲骨文送給我;這是我收集古今書畫的第一張。 董興兄畢業後到美國改行讀城市設計,現任職費城市政府,我們也間中相訪,時經四分之一世紀的情誼,是多麼可貴! 印尼僑生佘登淵兄,是個舉重的好手,當選過「臺灣先生」。由於當年印尼政變,畢業後沒有返回僑居地,卻到了香港,在一間日本貿易行當會計,受盡倭奴的氣。有一次,那個倭奴主管又辱罵他,實在忍不住,嗖的一拳就打出去,把那倭奴的鼻子打得稀巴爛,然後回罵一頓,不幹了。他在非常困苦的生活中掙扎,後來買到一部輾銅絲的舊機,把爛銅爛鐵投進去,輾出了一個一個的鋼鐵絲球,賣給人家擦爐鍋炊具。就憑這一部生產舊機和他不眠不休的努力,終於穩定下來,而且漸有積蓄,以後兼營臺、港貿易。我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回國,他已是全國有數的大貿易商了;獨資主持國際貿易大樓的艾達貿易有限公司,也是他的大本營。他的董事長室,少說也有八百方尺,其他陳列室,職員辦公室的面積,就可想像了。我們有一次晚飯。談起當年彼此的克難事,都覺得可笑。他講打「架仔」的事,更興高采烈,認為這是決心的一拳,置死地而後生的一拳,有了這一拳,才為後來自己打出了天下。這一拳打對了,但日本人的鼻子卻爛了。 向祖國告別 我們全系中長得最矮的,也許是李永晃兄吧。但他的體力強健,身手靈活;他皓愛體育,還是美式足球的好手,常常代表我們的學校出賽。 他和我的交情很不錯;他沒有到外國,服役後就出社會服務,現在是臺灣「味全」的經理。他到現在還是熱情如故,豪飲如故的人。早幾年,我們幾位好友在臺北一家著名的酒家飲酒敘舊,大概大家也喝得差不多了,偶而東倒西歪之餘,少了應有的服務。李兄叫侍應生給他來一個最厚的菜碟,放在左掌上,他舉起右手作刀,當中斬下,厚碟應手兩段,隨手滑落,就在那一剎那,他兩手往下一抽,截回兩邊的斷碟,沒有墜地。我們醉薰薰的鼓掌叫好,那些侍應再不敢離開我們,他也滿意地開喉大笑。 四年的時光過得真快,我突然感到學校的日子是多麼令人依戀,但時間是 不會停駐下來,讓我們多些日子相聚。隨著畢業試的完畢,學校就這樣擲下一張畢業証書,讓我們繞校園一團,就把我們攆出校門之外了。 這樣,讓我向校園邦一排排棕梠樹告別!也向合笑的杜鵑花告別吧! 向傅鐘告別;也向敲鐘的老人告別吧! 向一切愛護過、關心過我的人告別吧! 向所有克難的軍民們告別吧! 向祖國告別吧! 四川輪終於奏出驪歌,我站在甲板上,看到人們用顏色的紙條拋到岸上,送行者拾起來。紙條是繫不住蘭舟的。我從那裡來,回到那裡去吧!碼頭上挺看胸膛的青天白日旗,像向我揮手。讓我也說一聲:再見! |
|---|
| 2013年 許之遠 版權所有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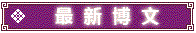
 你所在位置:
你所在位置:
